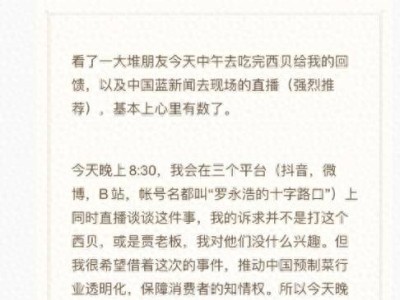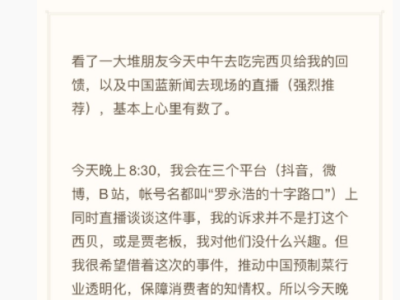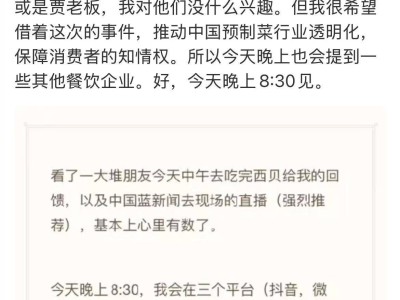在探讨智能机器人对人类劳动市场的影响时,一个常被提及的疑问是:如果大量工作被机器人取代,那么谁来消费商品?然而,这个问题或许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核心议题。
事实上,消费的本质并非由生产工具或生产方式决定,而是与社会的分配制度紧密相关。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五年内,人类或将深刻感受到AI对就业市场的冲击,正如历史上机械化、自动化对农业人口的替代一样。尽管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占比极低,如美国仅为1.3%,但这并未导致其失业率高于农业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如中国。2024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失业率为4.1%,而中国为5.2%。

面对AI带来的就业变革,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如何适应这一变化,而非单纯忧虑消费问题。例如,deepseek的深度学习研究员不仅未被AI取代,反而其薪资水平大幅提升。被取代的往往是那些简单的、重复性的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AI的崛起,不仅延长了人类的算力与记忆,更对教育体系提出了挑战,未来的教育将更加注重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培养。
然而,AI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不容小觑。与历史上的蒸汽机革命、电子革命相比,AI作为工具,其影响更为深远。它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更在深层次上重塑了社会的分配结构。李开复预测,未来15年内,50%的人类工作将被人工智能取代。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也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有4亿至8亿人因自动化失去岗位,新兴市场国家尤为严重。
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智能机器人取代人类劳动后,谁来消费商品?这实际上是一个分配制度的问题。分配主要包括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第一次分配由企业主导,取决于劳动的稀缺性;而第二次分配则由财政主导,这是关键所在。第二次分配的水平,直接决定了社会的民生保障程度,尤其是当大量一线工人失业时,一个国家的“人民性”将在此刻得到考验。
以德国为例,其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失业者提供了坚实的后盾。58岁以上的失业者可领取长达24个月的失业金,每月约合人民币1.3万元;还有公民津贴等制度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得消费问题迎刃而解。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市场的单位资本密度高,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在GDP中占比较高。相比之下,中国的这两项指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面对AI带来的挑战,人类未来的幸福不仅取决于第一次分配,更在于第二次分配的优化。通过提高累进税率、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措施,可以更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同时,向德国学习,建立公民津贴制度,甚至考虑马斯克提出的“全民基础收入”概念,都是值得探讨的解决方案。这些制度设计旨在确保每个人都有基本的消费能力,从而解决智能机器人取代人类劳动后的消费问题。

实际上,多国已经开始尝试“全民基础收入”的实验。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试点显示,受助者中37%选择重返校园,15%投入创业;芬兰的实验也表明,领取基本收入者的工作积极性并未下降,反而更倾向从事创意、护理等AI难以替代的职业。这些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让我们看到了解决消费问题的新路径。
智能机器人取代人类劳动后的消费问题,并非无解之题。通过优化分配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措施,我们可以确保每个人都有能力参与消费,从而推动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