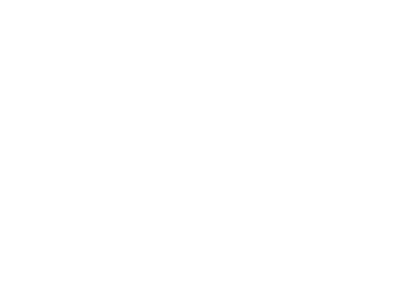站在全球能源版图的视角下审视,俄欧之间纵横交错的能源管道网络,不仅是能源运输的通道,更成为文明竞争的底层逻辑缩影。谁能够将“廉价且稳定的能源”精准输送至需求端,谁就能在时代变革中占据主动权。这一规律并非新发现,历史上英国依靠煤炭崛起、美国凭借石油称霸,本质都是对“资源调配”能力的极致运用。
2000年,美国学者彭慕兰曾提出一个颠覆性观点:一战前西方工业对东方的碾压,核心并非文化或制度优势,而是“获取煤炭的便利性”。以英国为例,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普及依赖煤炭,而伯明翰等工业重镇毗邻焦煤产区,运河与铁路的修建将运输成本压至极低。更关键的是,英国通过议会法案支持基建,私人资本投入铁路建设,全社会围绕“将煤炭送达工厂”的目标运转,最终构建起“资源+调配”的体系,为“日不落帝国”奠定基础。
反观同时期的清朝,江南作为经济中心,纺织、造船等产业蓬勃发展,但煤矿集中在山西、陕西等北方地区。受限于落后的运输网络——骡马驮运与漕船运输耗时数月,成本高昂——南方工业因缺煤而发展迟缓。晚清制度更无力统筹资源,地方势力割据、基建投入缺失,导致“有资源却无法送达需求端”的困境,成为工业落后的重要原因。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将这一逻辑推向新高度。石油取代煤炭成为核心能源后,美国通过大规模基建将全国石油网络串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得克萨斯州的石油通过管道与铁路快速运至东北汽车厂与东部炼钢厂,将成本压至全球最低。更关键的是,美国将石油与美元绑定,构建“石油美元体系”,使能源从商品升级为金融武器,最终巩固全球霸权。而彼时的中国,既未抓住煤炭时代的机遇,也未搭上石油霸权的快车,工业差距逐渐拉大。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重心向东南沿海转移,珠三角、长三角凭借港口优势成为“世界工厂”,但能源难题随之浮现。与清朝类似,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集中在西部的新疆、陕西、四川,而东部工厂与家庭的能源需求迫切。更严峻的是,中国人均石油储量仅为全球平均的8.3%,工业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北非的动荡导致油价波动,2008年国际油价飙升至147美元/桶时,国内依赖石油的中小企业成本激增,部分工厂甚至濒临倒闭。
运输风险同样不容忽视。油轮需经亚丁湾、索马里海峡与马六甲海峡,海盗活动与航道安全受外部势力影响,进一步加剧能源供应的不稳定性。这种“被能源卡脖子”的困境,比技术封锁更致命——工业链的每一环节都依赖稳定的能源供给。
面对挑战,中国未选择被动应对。上世纪末启动的五大世纪工程中,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直指能源困局,而2004年特高压技术的突破,更成为破解难题的关键。特高压的核心逻辑是“西部转化资源为能源,再输送至东部”:在内蒙古煤矿旁建电厂,将煤炭转化为电力,通过±1100千伏线路数千公里输送至上海、广州。相较于传统铁路运输煤炭需3天,电流传输仅需15分钟,且减少了运输损耗与污染。
特高压技术的战略价值远超经济账。若继续依赖进口石油,航道被封锁将导致工业链瘫痪;若持续运输煤炭,污染治理成本将不堪重负。而特高压使中国摆脱对“运油通道”的依赖,将西部能源直接转化为东部生产力,实现从“被动购买”到“主动构建体系”的转型。目前,中国特高压技术全球领先,输电效率超90%,适应从沙漠到水乡的复杂地理环境,为能源安全筑起坚实屏障。
中国的能源布局更着眼于未来,其关键在于打破“胡焕庸线”——这条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的地理分界线,东侧占全国36%的土地却居住着96%的人口,西侧资源丰富但开发滞后。新能源的崛起为西部带来“弯道超车”的机遇:西部的风能、太阳能资源占全国80%与90%,过去因运输难题难以利用,如今通过特高压与储能技术,可将“风”与“光”转化为电力输送至东部。
十四五规划中的九个大型清洁能源基地,七个位于西部,如甘肃酒泉风电基地、青海塔拉滩光伏基地,已成为“西电东送”的主力。这些基地不仅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更带动西部基建与就业:修路、架电网、建设光伏板生产厂,为当地创造大量岗位。例如,甘肃的光伏板厂让居民在家门口就业,同时光伏电站的固沙作用实现生态与发展的双赢。
新能源战略还巩固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尽管印度、越南劳动力成本更低,但其电力依赖进口煤炭或不稳定的水电,电价高于中国。西部新能源的普及使中国整体能源成本下降,叠加完整的供应链优势——如东莞电子厂所需零件可在周边城市配套——制造业根基得以稳固。印度、越南的劳动力优势被中国的能源优势抵消,产业转移的威胁随之降低。
中国的能源战略并非简单追随潮流,而是一套“破局组合拳”:既解决历史遗留的能源困局,又激活西部发展潜力,更稳固制造业优势。与英美通过“抢夺资源、控制通道”的老路不同,中国依靠技术创新与体系建设,走出一条可持续的能源发展道路。当全球仍在为传统能源争斗时,中国已在新兴领域开辟新空间,或许也为人类摆脱“能源战争”提供了新思路——文明的进步,终究要靠更远、更稳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