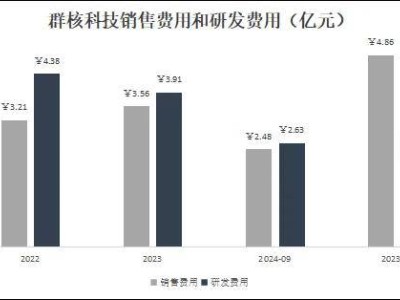酱酒行业经历风云变幻,新时代格局初现端倪。
近年来,酱酒在白酒领域的市场份额显著增长,从原先的20%跃升至30%,众多酱酒品牌借此东风,实现了从二线到一线贵族的华丽转身。然而,这场“酱酒热”带来的不仅是机遇,还有挑战与风险,诸如茅台之后的次席之争、稀缺产能的激烈竞逐、泡沫经济下的掘金冒险等。
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酱酒市场逐渐从混乱走向有序,从群雄逐鹿演变为巨头割据,从遍地黄金的淘金热进入大浪淘沙的新阶段。新时代的酱酒,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
热潮退去,酱酒回归平凡。日前,权图酱酒工作室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酱酒产能约为65万千升,同比下降13.33%,这是自“酱酒热”以来产能的首次下滑,标志着酱酒退潮期的到来。销售收入虽同比增长4.35%,达到2400亿元,利润也微增3.19%,达到约970亿元,但整体增长势头已明显放缓。
追溯“酱酒热”的起源,已难以找到明确的界限。或许是从茅台净利润登顶白酒行业开始,又或是茅台确立行业龙头地位之时,再或是郎酒、习酒等品牌以“酱酒第二股”之争迅速崛起之际。但真正让“酱酒热”进入爆发期的,是2020年疫情期间,以茅台为首的酱酒品牌展现出的强大抗风险能力。
“酱酒热”本质上是市场需求对产业供给的诉求体现。热潮之下,酱酒产能迅速扩张,2020年至2023年间,酱酒产能从60万千升增长至75万千升,其中2022年同比增速一度高达16.70%。尽管2023年增速放缓至7.10%,但仍保持增长态势。这与白酒行业整体的下滑趋势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2024年酱酒产能的阶段性首跌并未出人意料。自2021年茅台酒批价回调以来,酱酒行业已步入调整期,资本撤退、市场整改、酒商崩盘、价格滑坡等现象频现,预示着行业高楼可能面临的坍塌风险。
2024年,酱酒明星大单品的市场成交价普遍下降10%-20%,飞天茅台的价格也从3000元左右的高位跌至2200元左右。同时,各主销价格带的酱酒产品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中高端、次高端、高端、超高端酱酒的价格带均有所调整。权图酱酒工作室预测,若消费市场持续恶化,这些价格带还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酱酒市场的价格回调,意味着酱酒已从繁荣时期的狂热回归平凡。以高价著称的酱酒,如今不得不与其他香型白酒展开贴身肉搏。
行业出清加速,巨头之争愈演愈烈。自“酱酒热”爆发以来,酱酒行业格局经历了巨大变化。2019年,酱酒行业还是“茅台+其他酱酒”的格局;而到了2024年,“一超多强”的酱酒版图已基本定型。贵州茅台以超过1700亿元的营收遥遥领先,习酒、郎酒两家超200亿规模的酒企稳居第二梯队;贵州珍酒跨越50亿门槛,向百亿目标迈进;国台、茅台保健酒、金沙窖酒等酒企则守住“酱酒名流”的门槛。
在这之后,是钓鱼台、湖南武陵、广西丹泉等多家小型酱酒企业在队列尾部激烈竞争。从“酱酒热”爆发到红利退潮,格局稳固的同时也意味着“低头捡钱”的时代已经结束。那些曾经高喊百亿目标、宣称“酱酒第二”的酒企们,有的已崭露头角,有的则沉入水底。
酱酒团队的缩减,是酱酒产能大幅下降的根本原因。据权图酱酒工作室调研数据显示,2024-2025年生产季,仁怀等主产区的地方主流酱酒企业和中小酱酒企业减产停产超过15万吨。相比之下,头部酱酒企业加上部分业外产业资本整体增产5万吨,才将酱酒产能的减产量缩减至10万吨。

未来,我国酱酒有效产能将保持在60万-70万吨之间,供给市场的酱酒产能将维持在50万千升左右。其中,80%的产能将由酱酒企业的TOP10占有,中小酱酒企业的产能大部分将永久出清。
在头部酱酒企业稳产扩张、后排出清的背景下,酱酒角逐最终将走向“巨头游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后排玩家完全没有生存空间。在“大而全”的光环之下,“小而美”的差异化竞争策略依然能够展现出生命力。如李渡酒业通过“酒+文旅”模式推出高价光瓶酒,玉泉酒业等区域酒企则通过“产城融合”聚焦本土文化,形成不可替代性。

在酱酒领域,做精做细同样会成为中小酒企转型的重要路径。金酱酒庄成为首家获得中国特级白酒酒庄荣誉的酒庄,云门、古贝春、秦池等山东酱酒则依托“鲁派酱酒”地理标志,联合行业协会制定团体标准,强化产区认同。

然而,权图酱酒工作室也指出,只有极小部分中小企业能够成功转型为精品酒庄和圈层品牌。产能小并不代表就是精品酒庄,精品酒庄需要完整的精品酿造、年份储存、圈层品牌、深度体验等闭环。这要求想要打造精品酒庄的中小酱酒企业主动转型,实现经营创新。
相比之下,贴牌酒的命运则更为坎坷。白酒营销专家肖竹青表示,受行业调整影响,“酱酒热”带来的新增产能无法消化,以“贴牌”“定制”为主营业务的小酒厂因缺乏消费者认知和品牌建设,逐渐边缘化甚至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