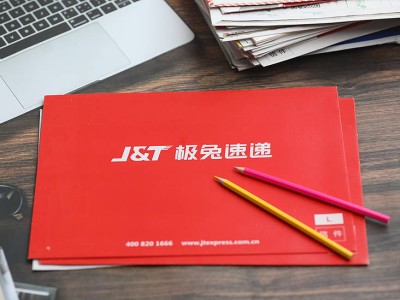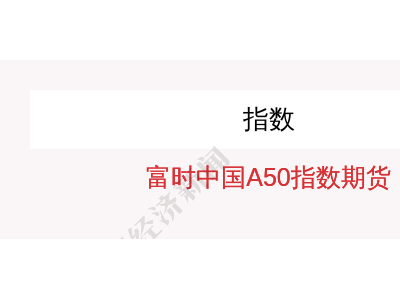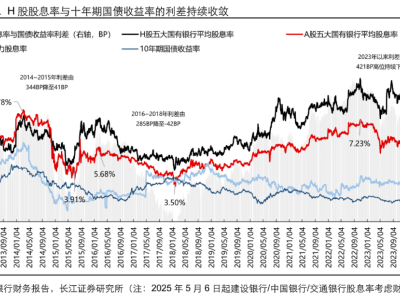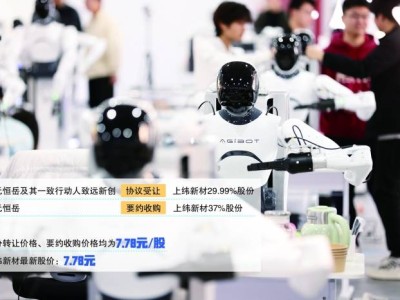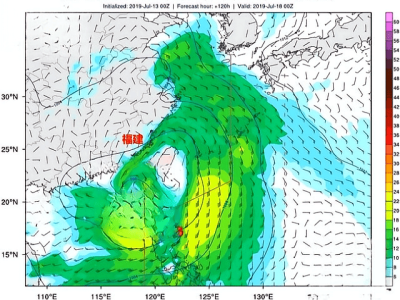近日,国内知名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再次传出将被腾讯音乐收购的消息,据某些媒体报道,与三年前相比,喜马拉雅的估值已大幅缩水。对此,喜马拉雅官方回应称,对“卖身”一事并不知情。
播客行业在国内发展多年,从最初的创作者个体到如今各大平台纷纷入局,中文播客领域究竟谁在盈利?随着B站、小红书等视频平台的加入,播客赛道是否能迎来新的转机?
自播客形式诞生以来,其内容已涵盖多种叙事风格。观察各大播客平台的热门榜单不难发现,最受欢迎的节目大多集中在“惊悚悬疑”、“女性权益与商业讨论”等几大类型。例如,近期因欠薪事件登上热搜的《不合时宜》播客,便是一档以女性视角探讨文化的节目。
不同种类的播客在变现方式和效率上存在显著差异。灵异、罪案类故事因收听门槛较低,受众广泛,更容易在付费专辑上取得成功。例如,经典鬼故事IP《张震讲故事》在喜马拉雅的付费专辑售价高达99元,其中一档播放量已超过五千万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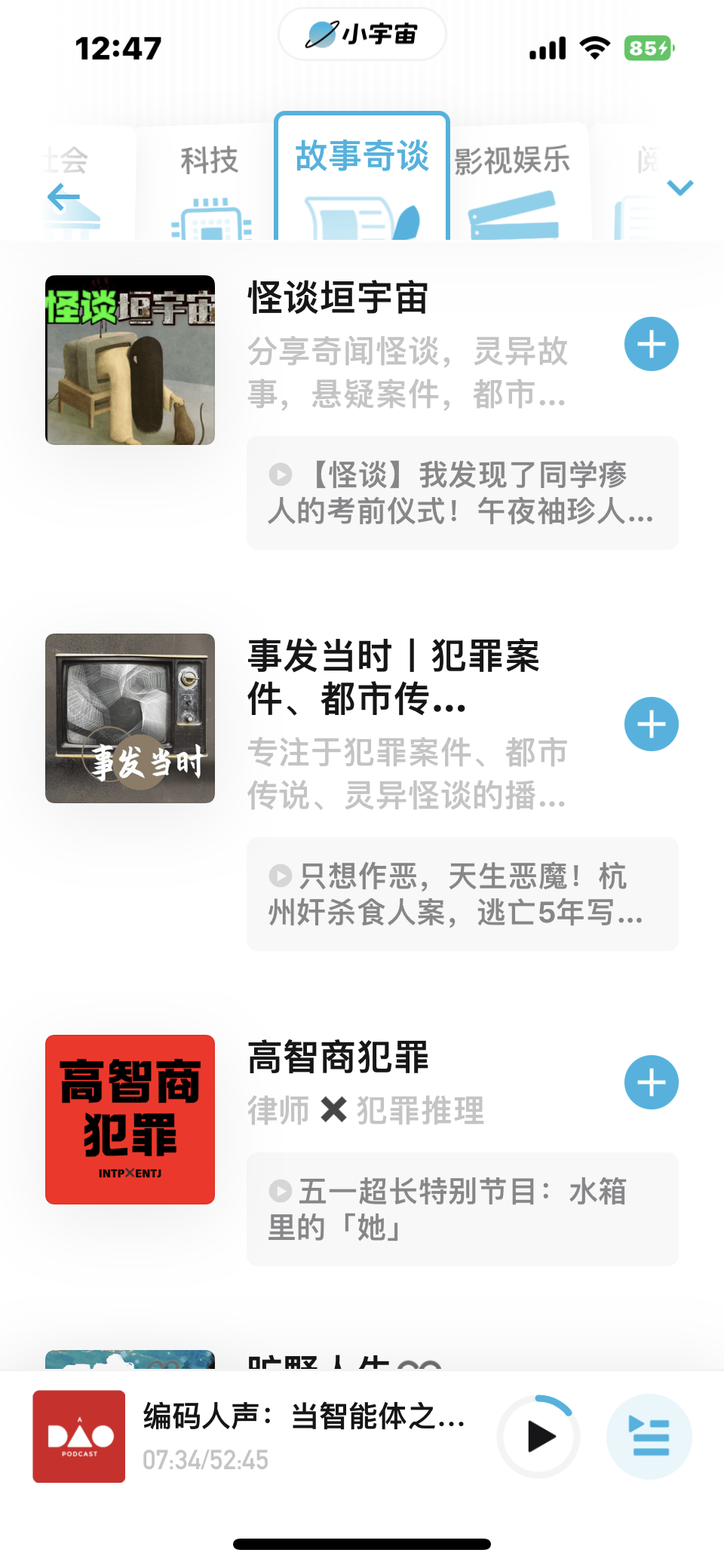
然而,对于商业和文化漫谈等较为严肃、收听门槛较高的播客,付费收听模式则不太奏效。一位有着八年科技主播经验的播主凤仪(化名)坦言:“大家上了一天班已经很累了,谁还想花钱听课?不如听点有趣的放松一下。”
尽管如此,商业与文化类节目仍是播客领域的主流。据Just Pod发布的《2024中文播客新观察》数据显示,在拥有超过一年制作经验的创作者中,仅有24.6%尝试过付费节目。除了鬼故事外,平台上热卖的付费节目大多依赖于主播个人IP的影响力,如梁文道的《八分半》、杨天真的《高情商公式》等,付费听众人数均过万,而原创播客团队的付费节目则难以达到这一水平。
因此,“商业与女性话题”类的严肃播客多选择品牌合作作为变现方式。播客用户对软广告的接受度极高,Just Pod的报告显示,仅有0.6%的听众在听到广告时会选择退出节目,有近30%的听众会选择听完全部广告。
一些奢侈品牌在“小宇宙”上的年度预算甚至接近千万级别。受限于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监管的情趣品牌、药企、保险公司等也对播客这一媒介表现出浓厚兴趣。不同声量的播客在报价上存在显著差异,头部播客单集报价通常在10至20万元之间,而腰部和尾部主播的报价则参差不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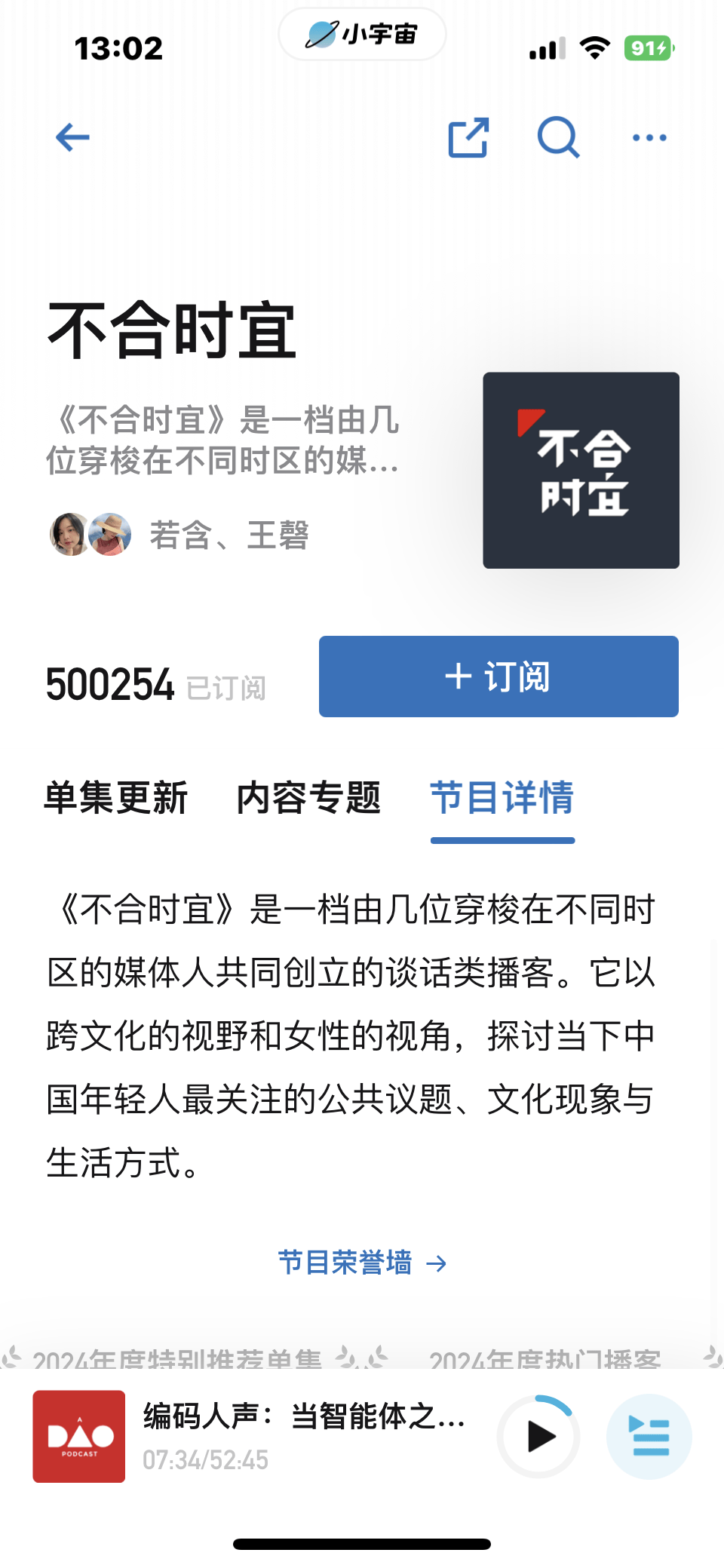
除了品牌合作和付费节目,部分播客也在尝试向私域引流或帮助品牌举办线下活动等方式变现。但整体来看,“赚钱难”仍是中文播客创作者面临的最大挑战。狂喜播客节创始人关雅荻表示,绝大部分播客节目目前仍难以盈利,这几乎是行业一线从业者的共识。
在《不合时宜》的欠薪风波中,令众多网友震惊的是,头部播客团队的报价远低于短视频和公众号图文领域的头部创作者。微信公众平台和小红书上的头部账号,商务报价不乏40万元以上,几乎是《不合时宜》单集商务报价的三倍。
这一收入落差一方面源于播客赛道本身的规模较小,另一方面也与播客平台整体的商业化程度滞后有关。尽管播客拥有“精英”属性,聚集了一批优质用户,但这也意味着播客一直未能真正走进大众市场。Just Pod的报告显示,国内播客听众学历高、消费能力强,主要集中在更具消费活力的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平均月收入为16136元。
据央视财经信息联播节目《播客新“声”机》调查显示,2024年以来中文播客节目的数量较三年前增长了六倍,中文播客的听众数超过2.2亿。尽管近几年播客“复兴”,用户增长迅速,但用户总量及月活与抖音、B站等视频平台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用户体量限制了市场规模的天花板。根据Statista的报告,2024年中国播客广告市场收入约为33亿元,仅是短视频平台一年广告收入的零头。类似于《不合时宜》这样以兼职为主、佛系运营的小型创作团队在播客市场比比皆是。据了解,国内全职进行播客创作的作者仅占约20%,大部分创作团队都是依靠“为爱发电”的热情持续更新。
播客商业价值的尴尬,平台难辞其咎。喜马拉雅、荔枝FM、网易云等互联网音频平台都有播客频道,其中喜马拉雅的用户基数最大。据喜马拉雅去年更新的招股书显示,2023年喜马拉雅全场景平均月活跃用户达3.03亿,移动端平均月活跃付费用户达到1580万,占据国内音频行业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然而,这家国内最大的音频平台直到2023年才实现扭亏为盈。喜马拉雅2024年上半年第三次向港交所更新招股书,2021至2023年期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58.57亿元、60.61亿元和61.63亿元,调整后净利润分别为-7.18亿元、-2.96亿元和2.24亿元。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该招股书已失效。
“原创播客”本是喜马拉雅近两年重点拓展的板块,但近期有员工对媒体表示,由于盈利压力,播客作为内容型业务,在内容层面投入反而较为保守。喜马拉雅的主要收入来自会员订阅,随着公司重心放在“拉会员”上,2025年第一季度,播客业务的核心指标已从DAU增长、用户消费频次等转变为“只看商业化”。接下来,喜马拉雅很可能会加快调整站内播客的商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