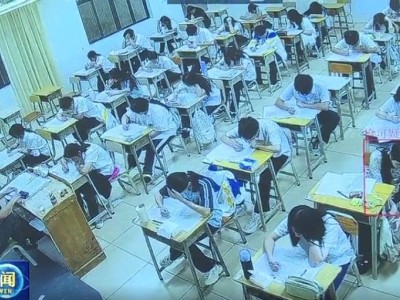在港交所上市的众多中概互联企业中,腾讯音乐以其独特的地位和表现引起了广泛关注。作为一家互联网龙头企业的控股子公司,腾讯音乐员工总数仅约5000人,但其人均市值却紧随母公司之后,在中概互联企业中名列前茅。其市值规模甚至接近7个微博、3个B站、1个贝壳,甚至约等于3/4个百度,这样的市场表现无疑令人瞩目。
腾讯音乐作为腾讯的控股子公司,业务相对单一,却能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市场中脱颖而出。仔细研究其近年来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腾讯音乐是一个隐藏在巨头背后的实力派选手,同时也是一个非典型的垂类赛道龙头。那么,它的“非典型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腾讯音乐的“第一怪”在于其越监管利润率越高。在过去十年间,音乐平台的版权问题,尤其是“独家”版权争议,经历了多轮监管和整改。然而,在丧失独家版权的情况下,腾讯音乐的毛利率却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在反垄断政策实施后,腾讯音乐作为用户基数最大的企业,在发行商与内容供给商的博弈中重新占据了优势地位。尽管用户流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市场份额,但并未对其整体价值造成直接影响。
其次,腾讯音乐的“第二怪”在于其用户越少用户价值越高。自2020年以来,腾讯音乐的在线音乐业务和移动社交娱乐业务的月活跃用户数均出现了下滑趋势。然而,与此同时,其在线音乐业务的用户平均收入(ARPU)却出现了上涨。这表明,腾讯音乐在用户群体上实现了“提纯”,留下来的基本都是愿意付费的高净值用户。相比之下,同为国内TOP2的音乐平台网易云音乐,尽管用户规模持续增长,但ARPU却出现了下降趋势。这种单位用户价值的巨大差异,无疑彰显了腾讯音乐在用户运营方面的独特优势。
再者,腾讯音乐的“第三怪”在于其挣得越多花的越少。近年来,腾讯音乐在保持营收稳定增长的同时,整体费用规模也出现了明显下降。这主要得益于其议价权带来的红利以及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费用降低、利润抬升,使得腾讯音乐的归母净利润实现了大幅增长。同时,其账面高流动资产也增长了近百亿,账面现金余额达到了约285亿元。这样的财务状况无疑为腾讯音乐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腾讯音乐这些“怪”现象呢?这或许可以从经济学角度进行解读。艾伦·克鲁格在《摇滚吧,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许多违反典型经济学传统的观点,这些观点或许能够恰如其分地阐释腾讯音乐的反常之处。例如,“长尾经济”悖论解释了为何在互通99%版权后,腾讯音乐的利润反而更高;双重伴随性则揭示了音乐作为一种内容形式的独特魅力和广泛应用场景;而跷跷板经济则解释了为何腾讯音乐能够在削减费用的情况下依然保持较高的活跃用户规模和内容供给。
腾讯音乐的股权结构相对简单且集中,母公司腾讯占据了绝对控股地位。这使得腾讯音乐在资本运作和利润分配方面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尽管其历年来回购比例和次数远高于分红,但这或许可以视为另一种回馈投资者的方式。毕竟,对于手握大量现金的腾讯音乐来说,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资金进行业务拓展或回馈投资者,将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腾讯音乐之所以能够在互联网市场中独树一帜,主要得益于其独特的业务模式和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同时,音乐产业作为一个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也为腾讯音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随着消费者对于优质内容和故事的需求不断增加,腾讯音乐有望在这一领域继续发光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