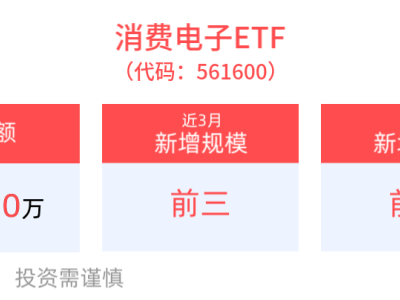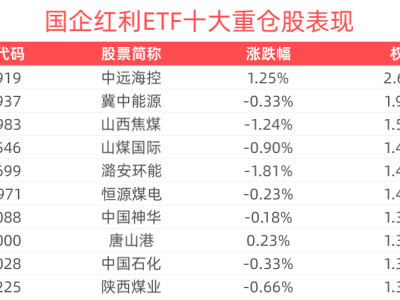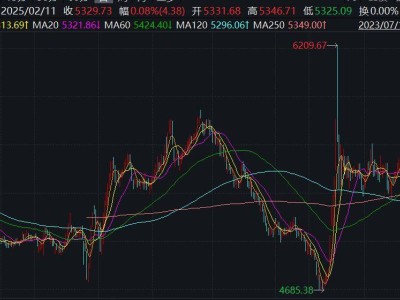近期,社交媒体上疯传的一段聊天记录引发了广泛讨论。这段记录来自韩束母公司上美股份的创始人吕义雄,他在工作群中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观点:利用AI技术替代大部分员工,仅保留少数能够熟练使用AI的人员。
具体而言,吕义雄建议法务部门裁员50%,仅保留20%能熟练使用AI的员工;客服部门裁员比例更是高达95%,只保留5%的人员;新品创新中心也将有70%的员工面临淘汰。尽管吕义雄后来在朋友圈解释称公司并非真正裁员,且今年总人数将增加800人,但这一解释并未否认聊天记录的真实性。
实际上,关于AI可能引发的大规模裁员,早在2023年AI大模型崭露头角时,就已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热议。当时,几乎所有创业者都被问过如何看待AI带来的人员替代问题,而他们的回答也几乎如出一辙:技术变革虽会导致部分岗位消失,但最终会创造更多新的就业机会。然而,随着AI技术更广泛地融入工作和生活,人们逐渐发现这一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
AI带来的挑战不仅限于人员替代,更关乎一个文明社会在时代进步过程中的价值取舍。它要求我们思考如何照顾社会的“弱者”,如何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的体面与尊严。
上美股份的案例并非孤例。例如,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在看到内部接入deepseek的程序生成的测试结果后,当场表示将淘汰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程序员。而在欧美国家,因AI导致的裁员新闻更是屡见不鲜。
Salesforce的创始人兼CEO马克·贝尼奥夫在谈及公司2025年的规划时提到,由于AI显著提高生产力,Salesforce在2025年将不再招聘任何软件工程师。他透露,Salesforce已推出名为Agentforce的AI平台,企业可在上面自主创建智能体,这些智能体能在酒店、医院等场景24小时不间断工作,并能与人类协作。贝尼奥夫表示,2024年Salesforce利用Agentforce和其他AI技术将生产力提高了30%以上。

同样,OpenAI的创始人兼CEO萨姆·奥尔特曼也在年终总结中写道,他相信2025年将看到第一批AI代理加入劳动力大军,并从根本上改变公司的产出。Salesforce公布的最新成果显示,在截至1月底的第四财季,其Agentforce AI产品已录入数千笔交易。
更大规模的人员替代其实早已开始,客服行业首当其冲。全球最大的分期购物公司Klarna是AI的坚定实践者。早在2023年,Klarna就开始与OpenAI合作,基于ChatGPT创建智能客服。到2024年初,Klarna在全球23个市场、涉及35种语言的客户服务中,已有三分之二由机器人接管,相当于700名全职员工的工作量。

机器人的效率极高,不仅降低了错误率,还使平均对话时间从11分钟缩短至2分钟。受此影响,Klarna在2023年冻结了招聘,并在2024年表示希望在未来几年内将员工人数从最高峰的5000人缩减至2000人。Klarna的联合创始人兼CEO塞巴斯蒂安·西米亚特科夫斯基坦言:“我们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
AI确实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同时也带来了广泛的人员替代和失业问题。除了Klarna,全球范围内许多客服相关岗位都面临裁员的挑战。例如,亚马逊、Charter等公司也相继裁员,其中不乏客服岗位的员工。
高盛估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可能会在写作、翻译和客户服务领域取代或影响3亿个工作岗位。尽管一些企业表示,AI取代部分岗位后,剩余员工将获得更高的收入,但这一观点显然并不具备说服力。因为只要AI淘汰掉的低收入员工足够多,剩余员工的平均薪酬即便不涨,也会大幅提高。
那么,AI在取代一部分工作岗位的同时,是否创造了更多的新工作岗位呢?答案肯定是有的。例如,浙江省宁波市近期就开启了首个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项目,首批有40余名学员报名。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也显示,人工智能和数据处理技术将创造1100万个新职位,但同时也会取代900万个工作。

然而,这一结论忽视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AI创造新岗位的速度是否超过取代旧岗位的速度;二是被取代岗位的员工是否能胜任新岗位的要求。例如,meta在计划裁员的同时,也在加快招聘机器学习工程师,但被裁的员工显然无法立即胜任这一岗位。
AI带来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尤其体现在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平均线以下的群体。呼叫中心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欧美大型企业过去常选择在印度、东南亚等劳动力廉价地区建立呼叫中心。然而,现在这些岗位正面临被AI替代的威胁。牛津经济研究院和思科的研究估计,到2028年,数字自动化可能导致菲律宾11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
AI不仅冲击外包岗位,更广泛的职位如程序员、文案、设计、策划等也同样面临威胁。因此,AI对人们工作带来的影响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大得多。